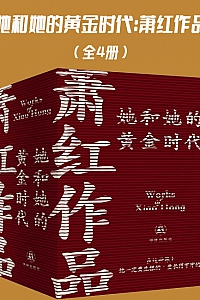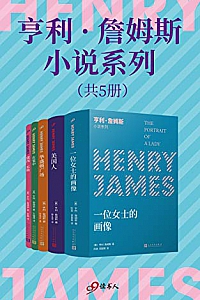《陈丹青音乐笔记》

内容简介:
《陈丹青音乐笔记》这本集子,是1992年到1998年间,作者远远躲在纽约寓所陆续写给上海《音乐爱好者》双月刊的十几篇文章,包括“灵堂琴声”、“告别交响乐”、“赴死的演奏”、“外国音乐在外国”、“阶级与钢琴”等篇。这些文章是作者说些纽约的关于音乐的见闻。
作者简介:
陈丹青,1953年生于上海。
1970年初中毕业,先后在赣南、苏北插队落户八年,其间自学绘画。
1978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。
1980年毕业,留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任教。
1982年初自费留学美国,以自由职业画家身份定居纽约至2000年。
2000年春,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邀请回国,为2000年清华大学百名特聘教授之一,现任绘画系第四研究室责任教授。 [1] [2]
媒体推荐:
这本集子,是一九九二到九八年间,我远远躲在纽约寓所陆续写给上海《音乐爱好者》双月刊的十几篇文字。这些文字的读者,就我所知,一位是约稿的编辑,另一位就是我。现在,趁这集子的出版,我要特意向那位约稿的编辑鞠躬致谢,为什么呢,因为经他的撩拨,我从九年前开始了持续的写作。
写作,我一向喜欢的,但除了就学前后的所谓“创作谈”,以及不像文论不像批评似的零星稿约,二十多年间仅只发表过可数的几篇,内容不出美术的范围,美术以外的话题,哪里梦想过呢,然而做梦似地,去年以来,我竟写成两本“书”,一本是已经上市《纽约琐记》,一本是尚且搁着晾着的《多余的素材》。内容不论,书写的文体,勉强算是“散文”或“随笔”的意思吧,“文学”当然谈不上,但毕竟可以自视为“写作”,而从此在画画之外,多一招游戏骗骗自己了。画圈子里外或生或熟的朋友于是诧怪:你还写作?是的,我的那两本“书”之所以斗胆承应,居然写成,就是有这位编辑早早地就在催我动笔了。
我要谢谢他。且称他为Z君吧——九年前,是在深冬,我头一次回国省亲,在沪西一间极小的居室里遇见了Z君夫妇,吃饭聊天。得知他是弄音乐的,手上正编着《音乐爱好者》这本刊物,我就胡乱地说些纽约的关于音乐的见闻。不记得怎么一来,提起曾在曼哈顿寻看过霍罗维茨的丧仪,待讲到电影近镜头里老霍的大鼻孔怎样地悬着一滴鼻涕,Z君忽然打断我,高声说:哎呀丹青,你把这个写下来好不好?
我记得他一脸当真的表情。表情对我很起作用的。九年前,国中的出版业哪里能同今天比,Z君的兴致是在组稿,我的兴致是在写作:写什么呢,我自己并不知道,当有人给我指定了话题——譬如霍罗维茨的鼻涕——我就果然写起来,只是当初不想到后来会连续写下去,更别提拼凑起来出本书。
江南的屋子没暖气,其时我在地处北端的纽约呆了十一轮春秋,早忘了穿着棉袄夹裤在睡房里缩作一团的那份阴冷与寒气,可回国就为了怀旧呀,身体也在怀旧的。是在南京岳家的旧寓——现在早已拆成了一堆瓦砾——我泡杯滚烫的茶水暖暖手,用讨来的哪家医学院公文稿纸开始写,写完寄出,过几个月,就在纽约收到Z君寄来薄薄一册滴了霍罗维茨清鼻涕的《音乐爱好者》,同时他就催讨下一回的稿子了。
《灵堂琴声》算是我头一篇誊写干净拿去发表的文字习作,粗糙简单,还用“琴声”与“灵堂”搁在一起作题目,弄成小小的酸雅,骗读者注意,现在想来,真像少年时代头一回学抽烟,怕人看见,又想要人看见,手势、吞吐,尽在学架式。可是一根抽过,喉咙痒痒地也就接了第二第三根,虽是呛着咳着,也谈不上瘾,却不知不觉抽上口,不想戒了,何况还有个Z君频频给我递烟点火呢。
但我可从未有过谈论音乐的妄念,给Z君那么手指勾一勾,我竟不负责任写起来:所谓“责任”,是指我所没有的音乐知识,每篇所写,不过是些“关于音乐”的日常见闻,并不真在谈音乐;所谓“不负”,自然是指我一旦离谱太远,行家大约会对这“爱好者”的无知,付之一笑吧,而且那一笑,我看不见,不必非得脸红。Z君,则从不拆穿我的门外胡言,只管哄着我一期接一期写,这样子,六年期间给他写了将近十篇,到了九七年,有别家出版社约了我来写《纽约琐记》,又要回头谈论画画的事情,没有余裕了——九八年的《赴死的演奏》,是我给刊物的最后一篇,《瓦格纳问题》写写停停,竟忘了寄出去,现在可以收进来。